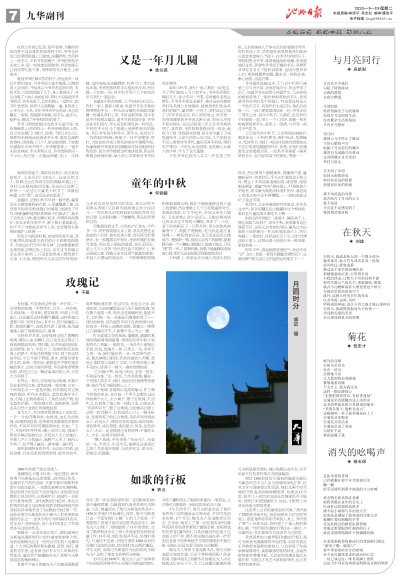发布日期:
2020年09月29日
如歌的行板
1869年的夏天想必很迷人。
基辅附近卡蒙卡村的一座庄园里,29岁的柴可夫斯基在这里度假,此时他已经是一名颇有名气的作曲家。从繁华都市莫斯科来到乡间农庄旅居,一切都是新鲜而充满野趣,连村里那个泥瓦匠干活时唱的小亚细亚民谣都那么悦耳好听,以致两年后,他创作一首弦乐四重奏的第二章《如歌的行板》时,那泥瓦匠唱的民谣立马回响在他的耳畔而被他巧妙而轻而易举地带进了《如歌的行板》第一节。此曲是柴可夫斯基作品中最为人们熟悉和喜爱的作品之一,也成为柴可夫斯基的代名词,甚至有人夸张地说,世人有时简直忘了作曲者还写过别的作品。
稍微有一点音乐常识的人,都知道柴可夫斯基是俄罗斯伟大的作曲家和旋律大师,而曾经稍微关注过一些传记历史的人也都知道,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在激越、悲怆、深沉、凄美的音乐里,还有着当时不太为人所知的乐界佳话,就是那个富孀梅克夫人和柴可夫斯基创造的精神神话。
有着多个孩子的梅克夫人优雅美丽酷爱音乐,第一次在朋友家听到一首《暴风雨》的曲子就被震撼,当她得知作曲者是柴可夫斯基,从此,她就活在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中。1876年冬他们开始通信,彼时,柴可夫斯基已由一个富有的矿主兼厂长的儿子变成一个需要别人资助才能完成创作的纯音乐人,梅克夫人出现了,给他提供了13年的资助,完成了俄罗斯音乐史上伟大作曲家的培育和成就工作。13年间,他们住得并不远,但他们相约,只通信不见面,有据可查的1200余封信是他们交流的全部,其间他们有过两次邂逅,并无交谈,而柴可夫斯基作为回报的是为梅克夫人创作了他有名的第四交响曲。13年后的1890年,梅克夫人由于身体和产业的原因不得不终止对柴可夫斯基的资助,并托人辗转带去了她的信和最后一笔资金。之后柴可夫斯基的一封封回信如石沉大海。3年后的冬天,柴可夫斯基完成了他所有的伟大创作随命运之神而走。不知可是宿命安排,2个月后,梅克夫人也追随音乐而去。去世前,她穿上了第一次在朋友家听《暴风雨》时穿的那件紫色天鹅绒长裙,音箱里放的是那首《暴风雨》,与其说她仍然沉迷于这首曲子的气势,倒不如说她沉浸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的那种超乎寻常的情绪里不能自拔。说她心里没有爱可能也无法解释。
梅克夫人资质丰艳高雅不凡,柴可夫斯基原本家庭优渥,后由于种种原因陷入经济困境,《暴风雨》让高傲不凡的梅克夫人决定拯救这位音乐天才,为了让高傲而敏感的柴可夫斯基接受资助,她以收藏乐曲为名,并不见面只写信委托柴可夫斯基编曲。
相信1200余封信从最初的编曲至最后无疑会向艺术与人生与情感纵深处扩张,但双方并无情感誓言和承诺,他们是两个对灵魂相守和追求的精神攫取者。如果说13年里,每年几十封信的交流没有情感是不可能的,但既已承诺便就相守,如此,才配得上对音乐纯美无瑕的尊重。
这世界上总有相通相亲的灵魂,“我听到了朝霞慈悲地升起,慈悲地照在白茫茫的雪地上,慈悲地照在那些苦难的人身上。我听到了勇气十足的生活,我听到了大地心脏的强烈心跳。”当听到《如歌的行板》这一章时,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为它流泪并为它留笔。
我更喜欢纯大提琴版《如歌的行板》,柴可夫斯基充满激情的华丽抒情,而带有管弦乐风格更有强烈的感染力,从而彰显了作曲家极端情绪化、忧郁敏感的性格特征,会突然郁郁寡欢萎靡不振,又会突然间满血复活充满乐观。可能这才是艺术家的特质吧,也正是我特别喜欢的。
基辅附近卡蒙卡村的一座庄园里,29岁的柴可夫斯基在这里度假,此时他已经是一名颇有名气的作曲家。从繁华都市莫斯科来到乡间农庄旅居,一切都是新鲜而充满野趣,连村里那个泥瓦匠干活时唱的小亚细亚民谣都那么悦耳好听,以致两年后,他创作一首弦乐四重奏的第二章《如歌的行板》时,那泥瓦匠唱的民谣立马回响在他的耳畔而被他巧妙而轻而易举地带进了《如歌的行板》第一节。此曲是柴可夫斯基作品中最为人们熟悉和喜爱的作品之一,也成为柴可夫斯基的代名词,甚至有人夸张地说,世人有时简直忘了作曲者还写过别的作品。
稍微有一点音乐常识的人,都知道柴可夫斯基是俄罗斯伟大的作曲家和旋律大师,而曾经稍微关注过一些传记历史的人也都知道,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在激越、悲怆、深沉、凄美的音乐里,还有着当时不太为人所知的乐界佳话,就是那个富孀梅克夫人和柴可夫斯基创造的精神神话。
有着多个孩子的梅克夫人优雅美丽酷爱音乐,第一次在朋友家听到一首《暴风雨》的曲子就被震撼,当她得知作曲者是柴可夫斯基,从此,她就活在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中。1876年冬他们开始通信,彼时,柴可夫斯基已由一个富有的矿主兼厂长的儿子变成一个需要别人资助才能完成创作的纯音乐人,梅克夫人出现了,给他提供了13年的资助,完成了俄罗斯音乐史上伟大作曲家的培育和成就工作。13年间,他们住得并不远,但他们相约,只通信不见面,有据可查的1200余封信是他们交流的全部,其间他们有过两次邂逅,并无交谈,而柴可夫斯基作为回报的是为梅克夫人创作了他有名的第四交响曲。13年后的1890年,梅克夫人由于身体和产业的原因不得不终止对柴可夫斯基的资助,并托人辗转带去了她的信和最后一笔资金。之后柴可夫斯基的一封封回信如石沉大海。3年后的冬天,柴可夫斯基完成了他所有的伟大创作随命运之神而走。不知可是宿命安排,2个月后,梅克夫人也追随音乐而去。去世前,她穿上了第一次在朋友家听《暴风雨》时穿的那件紫色天鹅绒长裙,音箱里放的是那首《暴风雨》,与其说她仍然沉迷于这首曲子的气势,倒不如说她沉浸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的那种超乎寻常的情绪里不能自拔。说她心里没有爱可能也无法解释。
梅克夫人资质丰艳高雅不凡,柴可夫斯基原本家庭优渥,后由于种种原因陷入经济困境,《暴风雨》让高傲不凡的梅克夫人决定拯救这位音乐天才,为了让高傲而敏感的柴可夫斯基接受资助,她以收藏乐曲为名,并不见面只写信委托柴可夫斯基编曲。
相信1200余封信从最初的编曲至最后无疑会向艺术与人生与情感纵深处扩张,但双方并无情感誓言和承诺,他们是两个对灵魂相守和追求的精神攫取者。如果说13年里,每年几十封信的交流没有情感是不可能的,但既已承诺便就相守,如此,才配得上对音乐纯美无瑕的尊重。
这世界上总有相通相亲的灵魂,“我听到了朝霞慈悲地升起,慈悲地照在白茫茫的雪地上,慈悲地照在那些苦难的人身上。我听到了勇气十足的生活,我听到了大地心脏的强烈心跳。”当听到《如歌的行板》这一章时,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为它流泪并为它留笔。
我更喜欢纯大提琴版《如歌的行板》,柴可夫斯基充满激情的华丽抒情,而带有管弦乐风格更有强烈的感染力,从而彰显了作曲家极端情绪化、忧郁敏感的性格特征,会突然郁郁寡欢萎靡不振,又会突然间满血复活充满乐观。可能这才是艺术家的特质吧,也正是我特别喜欢的。